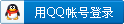早知蒋光照学长是交大校园的“编外教工”。他经常来交大校园看看,与交大的师生“同呼吸,共命运”。今天蒋先生正好准备在教师活动中心请几个朋友吃饭,我借此机会约他谈谈“交大情结”,他爽快地答应了。
初见蒋先生本人,他那高瘦清朗的外形,儒雅内敛的风度,才思敏捷的谈吐,怎么也让人想象不到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长者了。在教师活动中心刚一落座,利用等待蒋先生朋友的机会,蒋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蒋先生是“三句话不离交大校友”。蒋先生热心交通大学校友工作是出了名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他是最“铁杆”的交大校友。他1936年从当时无论从师资设备到教学质量都堪称全国第一的上海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所有学生心目中的首选——交通大学。在上学期间,他就立下了要把和所有交大校友的友谊保持终身的宏愿,但因连年战乱,联络困难,这个宏愿长期未达成。政治局势稳定后,蒋先生立即开始联络校友,并为五所交大的校友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坦率地说,我们很多人在求学期间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毕业后,面临创业的艰难、家庭的重负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绝大多数人就只能把大学友情放到内心最底层的角落,更谈不上东奔西走地为母校事业和校友联络倾尽全力。蒋光照先生却做到了。194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实业管理学系后,蒋先生离开了母校,开始创办实业。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始终没有忘怀跟交大校友的感情联络,还尽量对交大学生和校友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解放前,因为创业的需要,蒋先生移居台湾。从商之余,他始终关注着新竹交通大学的创办和崛起。2000年在美洲校友会的年会上,他又参与发起了全球交大校友联谊会,并亲任秘书长。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他就作为第一个返回大陆的台胞,定居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附近。为了母校的发展、校友的联络,他不辞劳苦,出资出力,牵线搭桥,甚至惊动了同为交大校友的江泽民总书记,在1993年竭力促成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所交大校长远赴宝岛台湾,与新竹交通大学校长共商协作和发展大计。从此拉开了五所交大校领导每年一次聚会活动的序幕,为本为同根生的五所交大加强兄弟之情,携手并进,创造了条件。为了使交通大学能争取到更多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和支持,促进母校办学环境的改善,蒋光照先生经常奔波于美国、大陆和台湾三地,联络校友,并以身作则,资助了许多项目。蒋先生不仅对学校的“有形资产”大力支持,更对学校“无形资产”的获得全力以赴。在他的帮助下,2003年底,曾获诺贝尔提名,有“半导体教父”之称的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台湾中研院院士施敏教授应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大大加强了学校的学术力量和声誉。蒋先生真可谓是功不可没。
聊兴正浓之时,蒋先生所宴请的朋友们来了。本以为是与蒋先生年龄相近的学长,没想到竟然是两位刚参加完毕业典礼的应届毕业研究生和一位家长,在我心目中蒋先生的形象更加和蔼可亲了。得知他们都已是多年熟知的“老朋友”了,我赶紧问问这些年轻人对蒋先生的看法。一位学生告诉我,每次去拜访老先生的时候,他总是要谈论很久交大的历史、校友的事迹和学校的发展情况,并且每次都要坚持请客吃饭。我们都忍俊不禁,蒋先生也憨憨地笑了。这些走出校门,已经荣升为交通大学最新一届校友的年轻人说,老先生对母校的执著之情早已经深深地感染了他们,他们也必将始终关切母校的发展和举措,并尽量回报交大的培育之恩。我深感像蒋光照老先生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校友才是交大无与伦比的财富,他们就像一块磁铁,吸引和凝聚了无数的力量,共同支撑起交通大学这个家。
学生们还告诉了我一个蒋先生“千里追书记”的有趣故事。蒋先生平时不仅热心学校事业,还特别爱提建议和意见,而且从不拖拉,有什么意见立刻要反映到相关领导。有一次,他急于向上海交大马德秀书记谈谈学校发展建议,但得知马书记近期事务极为繁忙而且马上要赴京开会。当马书记告诉他航班号后,他不顾行期极紧,票源紧张,利用熟人关系自费订购了同一班飞机的头等舱票,与马书记约好,想利用在飞机上的两个小时时间探讨工作。因马书记平日为节约学校开支,从来都是坐经济舱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虽然此次可通过“升等”免费转成头等舱,但不巧的是因头等舱客满未能换成。这次虽得以同乘一架飞机,却很遗憾地失之交臂了。蒋先生的率真执著由此可见一斑。蒋先生听我们在谈论这件事,忍不住插嘴道:“马书记是个非常能干而且有魄力的校领导,还是个很会虚心接纳意见,从善如流的人。其实要是五所交大哪个校领导某项工作做得不好,我也会毫不留情直接去“骂”的。”
蒋光照先生不失时机地又跟我们谈起了对学校教育工作的一些建议:交大应该不惜成本招贤纳才,特别是国际级别的学术带头人,这样才能有力地提高交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与国际高校的情况相比,国内高校领导在大量会议等繁杂低效的事务性工作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校领导要学会“不忙”,精简会议,严格控制会议时间;对于校友捐资,要舍得直接用本金操作,而保守地只用利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本金使用得好会促使更多的校友投资;校友会的最高层领导应该与学校领导脱离,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外部投资,也能对学校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校友工作对一个学校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工作量极大,学校现有工作人员人手不足,应该发动热爱学校的离退休老校友们参与校友会工作,而且教育基金会的捐赠资金使用情况经这些老校友们参与监督审核后,会进一步增加基金使用的合理性和透明度;对奖(助)学金的捐赠者的捐赠意图应充分了解,尽量安排捐赠者和受益学生的直接交流和长期信息反馈,使捐赠者及时了解捐赠效果;建议尽快给本科生使用英文课本,并规定教师必须掌握本专业英文知识,使本科生教学在最短时间内与国际接轨等等。
不知不觉,我与蒋先生已经聊了两个多钟头了。我被他的才思敏捷和强烈的交大情结深深吸引,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校友工作课。看到他忘我地投入对交大建设事业的关切,而又得知他的夫人因身体原因一直躺在医院里时,我感触良多。我们这些交大的校友工作者们如果没有做好这份工作,又怎能对得起交大校友这份沉甸甸的爱呢?最后我请蒋学长根据他与交大这么多校友交往的经验,说说交大培养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相比有何特色,本以为他会说“实干”之类的公认特色,结果他说:“交大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比其它学校的都深,交大校友的人数比国内任何大学的都多。”哈哈,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分手的时候,蒋先生说他要先到微电子学院去看一下施敏教授下次来校的日程安排,再去医院看他的夫人。我看着老先生渐行渐远的身影,突然感觉他象一杆修竹,虚心、坚韧,喜丛生,靠团结的力量抵御外力,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