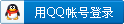——追思夫君杜庆萱
林云云
老伴走了,带走了他一生曾经辉煌的事业和那颗从海外归来,用整个青春年华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还有,我们那段曲折离奇的婚姻、相濡以沫四十余载至死不渝的夫妻情缘……
 从气温高达40℃的2010年仲夏到今年二月的西方情人节,他断断续续先后七次住进新华医院。在市委组织部领导和医院领导直接关怀下,组织了有关各科的专家参与会诊,并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开启了几无先例的人道救助的绿灯。 从气温高达40℃的2010年仲夏到今年二月的西方情人节,他断断续续先后七次住进新华医院。在市委组织部领导和医院领导直接关怀下,组织了有关各科的专家参与会诊,并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开启了几无先例的人道救助的绿灯。
老伴走了,每次住院他讲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家!”我没有能让他如愿,为此我自责不已。那张由他专坐的太师椅已人去椅空;小孙女常常用来当做麦克风,唱着“祝您生日快乐”的那根拐杖,如今孤寂地被搁置在墙角。
老伴走了,走得有些仓促,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我深知他平日的为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于是和儿子商量后达成共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在家设灵堂。然而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国内外发来的唁电、悼念文章和慰问信像垂怜我的春雨一样不断飘来,电话铃声也日夜响个不停……但孤灯、夜雨陪伴着我这颗沉沦苦海的心……
终将小林作大林
1962年的冬天,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第一个寒假,我回到上海探亲,同学的母亲陈伯母(陈伯伯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手下的一员将领)和银行家宋老先生替我做媒。据说对方是一位留洋回来的年轻教授,事业有成,一表人才。巧的是还跟我在同一所学校工作。初次的见面会约在南京西路的“凯司令”咖啡厅。我和宋伯伯提前到了。我正想看看这位年轻教授到底有多了不起,没想到等来的竟是大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男方的媒人,然后是年轻教授的父亲、姐姐,最后出场的才是主角他。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我不知所措。当这位年轻教授慢条斯理地问我喝些什么时,我的回答令所有的人感到意外:“冰淇淋!”寒冬腊月,他们要的都是热气腾腾的咖啡、红茶之类的热饮料。
然而,这场兴师动众的相亲“序曲”没有了接下去的“乐章”。可能是我的海外关系太复杂,他经常要出访前苏联及罗马尼亚等东欧“民主”国家,此事遭到组织的劝阻;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比他要小十几岁,不懂世故,不是块“贤内助”的料……
 十年离乱,我们各自都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我闻听了他家所遭到的惨祸,心中一直在惦念他。那时我已被送往干校劳动,我投石问路,大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的回信中的两句话,我至今还牢牢未忘:“云云同志:接到你的来信,犹如空谷足音……我现在还是孑然一身……。” 十年离乱,我们各自都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我闻听了他家所遭到的惨祸,心中一直在惦念他。那时我已被送往干校劳动,我投石问路,大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的回信中的两句话,我至今还牢牢未忘:“云云同志:接到你的来信,犹如空谷足音……我现在还是孑然一身……。”
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分别十年后的我们在唐山火车站候车室重逢了。此时,风流倜傥的他已英姿不再,一身灰不溜秋的棉袄棉裤,头上那顶棉帽子两边的“翼翅”随风啪啪作响。他手中还提着一个很旧的包,里面装着两个饭盒,他是佯装外出买东西向“造反派”请的假。
在一年多“地下工作”式的书信来往中,他总是称呼我为同志,而信的开头,我们都把毛主席的语录“活学活用”了,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到一个叫“永红桥”的办事处去登记,主管的老太太胸前佩了一个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上面还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因为我们都是“臭老九”,年龄相差又较大,好像注定有什么不轨行为,主管的老太太劈头盖脑地先训了我们一顿。 临了则很不情愿地将结婚证书发给我们,还搭上一句“好好改造”的赠言。大喜之日就碰到这样的晦气事,我好不扫兴,我老伴则无奈地劝我“从人屋檐过,不得不低头。”窗外滴水成冰,点缀我们新房唯一的喜庆之物,是我水栽在搪瓷碗里的一颗大白菜芯子。借助着室内微弱的炉火,倔强地抽出了嫩芽,开出米粒大的小黄花。还有一床用七条小毛巾打了七个补丁的丝绵被。 临了则很不情愿地将结婚证书发给我们,还搭上一句“好好改造”的赠言。大喜之日就碰到这样的晦气事,我好不扫兴,我老伴则无奈地劝我“从人屋檐过,不得不低头。”窗外滴水成冰,点缀我们新房唯一的喜庆之物,是我水栽在搪瓷碗里的一颗大白菜芯子。借助着室内微弱的炉火,倔强地抽出了嫩芽,开出米粒大的小黄花。还有一床用七条小毛巾打了七个补丁的丝绵被。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都要问我的老伴,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永红桥老太婆请‘吃排头’的日子……”
夜深了,我从抽屉中拿出一张宣纸,上面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两首诗,一首是:“春申一晤便钟情,几经蹉跎愧负卿。十年离愁意阑珊,终将小林作大林(darling)。”另一首是:“沧桑历经百事哀,西新(他的住所)非复旧亭台。雨后斜阳林荫路,翩翩倩影又重来。”
书香门第旺族后
 老伴出身名门之家。祖父杜钟骏是光绪皇帝的御医,曾撰写《德宗请脉记》一文。它生动、详尽地记载了祖父替光绪皇帝看病的全过程,是有关光绪医案所留下的唯一的珍贵史料,笔者以所记载的史实为依据,解读了这起晚清宫廷哀伤和苍凉的逸事。(2011年4月28、29日连载于本报阅读版)父亲是一位实业家,资深的民革 老伴出身名门之家。祖父杜钟骏是光绪皇帝的御医,曾撰写《德宗请脉记》一文。它生动、详尽地记载了祖父替光绪皇帝看病的全过程,是有关光绪医案所留下的唯一的珍贵史料,笔者以所记载的史实为依据,解读了这起晚清宫廷哀伤和苍凉的逸事。(2011年4月28、29日连载于本报阅读版)父亲是一位实业家,资深的民革
党员,曾任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杜氏有三兄弟(老伴排行第三),分别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机械和电机系,且都留学美国。老伴的侄女曾是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播音员杜宪,对她的朴实气度,柔美音色好评如潮,现被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聘为副教授。
秦岭山脉的丰碑
老伴生前为我国铁道电气化建设贡献卓著;为培养电气化高级技术人才著书立说,成绩斐然。
1942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远涉重洋留学美国。1948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应当时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之邀任副教授,此时年方28岁。他给学生教授的电力网络和高压电工课都是在美国学成带回的较新的课程。后来见他的讲课颇受学生的欢迎,王校长把自己讲授的电机工程这门课也交给了他。30岁那年,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聘他为正教授。
唐山工学院后改名唐山铁道学院,是我国培养铁道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基地。那时我国铁路运输主要是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老伴首次为学校开设了《电力机车》这门课程,并撰写了教材,该书后获铁道部优秀教材奖。
195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选派了50位科学技术人员随行,借此机会向苏联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电气化铁路技术资料的要求。随后中国组织了一个由铁道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及有关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电力机车考察团,于1958年初赴苏联考察,老伴担任考察团的副团长。
回国后他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于1958年11月18日,由田心机车厂负责试制的车体、转向架等机械部分组装完成,随后被送往湘潭电机厂进行总体组装。1958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辆6YI型电力机车在湘潭电机厂出厂,编号“001”号。由于生产厂家位于湖南湘潭,离毛泽东家乡韶山不远,老伴提议命名为“韶山号”,得到了首肯,此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一等奖。1975年7月10日,宝成线全线完成电气化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此项成绩被载入《宝成铁路修建记》一书。
如今韶山型电力机车仍为我国电气化铁路的主型机车。因此老伴的学生称他为“中国电力机车之父”。
1971年岁末,我随老伴由唐山内迁到四川峨眉。据说是根据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最高指示的大迁徙。当北方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四川盆地却是一片郁郁葱葱。我第一次乘坐电气火车跨越秦岭,神话般地进入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天府之国。列车蜿蜒于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涵洞,天堑变通途。
唐山铁道学院内迁四川峨眉后,改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校坐落在云雾缭绕的峨眉山下,没有大门,只有郭沫若题词的“天下名山”一块牌坊作为标记。一所蜚声海内外的古老学府,自由独立的学风、求真务实的校风日渐式微……
我们辗转南北数十载,历尽磨难。老伴作为人才引进,总算叶落归根,回到了上海。铁道部同意老伴调回,但不能出部。于是,老伴调入了上海铁道学院(后并入同济大学)。
淡泊人生也精彩
1990年,老伴70岁正式退休。韶光逝去,他犹如西坠的夕阳,逐渐告别了曾经辉煌的事业和人生。然而,生活的巨大落差并没有使他怨天尤人,而是用宽厚、包容换来了一颗平常的心。他把储藏室腾出一半作为书房,还起了一个很休闲的名字——退思斋。在此习字作画,自学成“材”。他的父亲是位收藏家,“文革”中被抄走的有董其昌、郑板桥、张大千、吴昌硕等人的名画。落实政策时发还的不是实物,而是每幅画折价人民币10元。他心疼的不是钱,而是国宝的流失。老伴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至今尚留有遗作百来件,虽不值钱,却凝聚了他后半生的心血。我不知道我死了后该留给谁?
退休前,老伴的工资是我的六倍,退休后我俩的养老金相差无几。为此我常发牢骚。他倒比领导还会做思想工作:“钱够用就可以了,每天拿着存折看零圈圈有什么意思?”他的衣食住行基本都是由我安排的,只是在他裤子的表袋里塞了200元钱,偶尔去福州路古籍书店买本书,我说这是他的“小金库”。患病期间,我把他的“私房钱”放到了他的抽屉里。如今,分文未动,我也永远不会再去动它……
结婚41年,他有三个“从不”:从不发脾气;从不发牢骚;从不对人说三道四,哪怕是负过他的人。只有两次例外,一次在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视片时,他忽然咬牙切齿地骂道:“日本鬼子最恘!”另一次则是嘲笑某自称“大师”的作家,他说:“没有人称他大师只好自己称自己了。”
老伴从没有“望子成龙”的那种奢望。他很少直接跟儿子对话,即使两人都在我身边,还要通过我这个“第三国”传话。儿子未成家前,做事总是丢三落四。买了东西忘记拿找头,拿了找头忘记拿东西,经常拿他爸洗脸用的香皂用来汏浴。于是,老伴在自己的肥皂盒边上贴了张“本人专用皂”的条子。为了防水还盖上一层透明胶带。儿子用过热水瓶总是乱放,老伴又画了张平面图,注明“热水瓶用后请按图示摆整齐”。儿子轻轻对我说:“阿拉爷用手画的圆像用圆规画出来的。”来客人时,我赶快将肥皂盒和平面图转向,要不怎么向人解释呢?
老伴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超脱的人格魅力,无形地在精神上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庭,影响并诱导着家庭的每个成员的为人之道。
桃李依旧笑春风
2008年10月,他曾任教的浙江大学电机系53届学生毕业55周年,为他寄来了集体照,还派了两位已年过八旬的学生专程来上海看望他,并送来一份专门给他留着的纪念品。
2009年11月,他曾经任教三十几年的西南交大电气工程学院举行了60周年院庆。邀请他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
2011年,他度过了90华诞。然而步入暮年的他,衰老逼近,疾病不断袭来,接二连三的半夜急诊,都是由我所在的民革的同志马天林律师从三楼背下背上,由于我儿子身材瘦小他该尽的孝道都由这位身强力壮的山东小伙代替了,为此我感到非常愧疚。在时任市委组织部领导周祖翼同志和新华医院党委书记孙锟同志的关怀及有关专家精心的治疗下,老伴艰难幸运地度过了他的九十诞辰。我在晚报“夜光杯”上撰写了《老伴过生日》一文。没想到文章竟被一位远在广州的六二届毕业的学生看到,他们的同学会辗转多处打听到了我家的通信地址,发来了祝贺老伴九十大寿的贺信。信中真挚地表达了对阔别近半个多世纪的师长的怀念。他们还风趣地回忆了以下的轶事:我们清楚地记得,是您给开的《电力机车控制》课程。当您夹着一个硕大的牛皮公文包走上讲堂时,同学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位教授服饰庄重、精神抖擞、仪表堂堂。别看您神情严肃,但您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由于您讲的我们容易接受,所以学得好,为我们后来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2年春节的大年初二,他又因高烧被送进医院,元宵节应当是合家团圆的节日,我把他接回家,总算吞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两颗元宵。2月14日西方情人节,他再次入院。一周后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我们各自去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了避免中国人那种不管你摔跤、打架、死人都来看热闹的陋习,我没有放声大哭,只是在老伴的额头和两颊轻轻地吻别,享受了人生最后的“浪漫”…… |